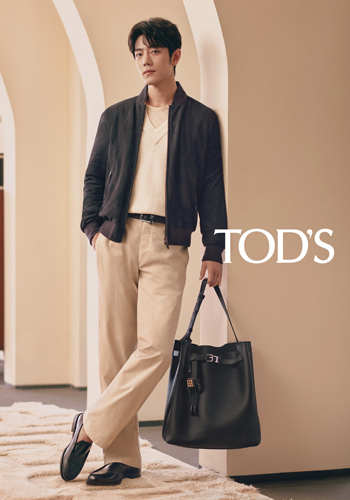感受书法的线条意味
毕加索,对绘画线条的非凡领悟是众所周知的。然而,就是这位顶级艺术大师说了一句让国人无比惊讶又无比骄傲的话:我不敢去中国,因为有个齐白石。
毕加索为何敬畏齐白石到如此地步?据说,毕大师的线条领悟源自齐大师的水墨灵韵。
齐白石,国画大师也。他无论画虾,画鱼,画紫藤,画绿柳,还是画白菜、萝卜,均神型兼备、意味悠长。白石老人堪称线条魔力大师。毕大师对齐大师的敬畏就在于此。
中国书画同源、同理,其源、其理均为充满神奇意味的水墨线条。
先辈告诉我们,要成为一个好的国画家,首先必须做一个书法家。道理何在?因为一个画家的“功夫”在于书法,在于对线条的领悟、把握和运用。
线条在绘画中更多呈现具象的造型,有一种“栩栩如生”的感觉,而在书法中则是抽象的组合。
中国书法艺术实则是线条的艺术。书法线条的产生,必须借助三样工具,即毛笔、水墨和宣线,然而仅这样还不够,还需借助于符号性文字材料方块汉字的结构造型,由书法家书写才能完成。
书法线条讲求人格化的形象意味和内涵,讲求情感意兴、意念的渗透和综合,追求“韵外之致”、“象外之象”。
书法线条的意味绝非生活和大自然的忠实描摹和机械复制,是非具象的,是抽象的造型艺术。
书法线条的意味跟用笔技巧和用墨功夫十分相关。书法线条的完成均依赖毛笔的恰到好处的运用,然而没有墨这个“现形剂”,“笔走龙蛇”的效果就无法呈现出来,一切精美的用笔皆无济于事。
在中国书法艺术领域,线条美的最高境界是线条的抒情内涵,而线条美的形式特征,我认为在于“三感”,即力感、质感和节奏感。这“三感”缺一则不完备。
书法线条最先抓住人心的形式美态是力感。在线条组合中,高超的用笔而表现的力感是扣人心弦的。它若是强烈、遒劲的,即会使你精神抖擞;若是柔媚、潇洒的,会使你心情舒适与和悦;若是曲折多变的,则会使你感到奇崛、跌宕。
力感盖因用笔的技巧与功力而不同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线条力度并不等于握笔的力度,并不是膀大腰圆的人使出浑身的蛮力就能造就强劲无比的线条,相反一个弱不禁风、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书生的书法,却会力感四溢、奇怪生焉。无他耳,只因为这个书生掌握了精美绝伦的用笔技巧。因此,书法线条之力并非蛮力,而是用笔的技巧之力。这是每个书家均晓知的。
线条的技巧之力究竟如何实现?这就需要深厚的“功力”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,非三言两语而能概述之矣。但在这里需要总结其中一些力的特征由来。一根线条的完成包括起笔、行笔、收笔三个基本动作。所谓起笔的特征是“逆”,书法启蒙老师常告诉我们“欲横先竖,欲竖先横”,是讲逆势起笔,而非顺势落笔,在线条中对“逆”的追求,其力度和厚度明显增强。所谓行笔的特征是“留”是讲在行笔过程中不能一笔飘过、轻浮华俏,需要“逐步顿挫”。所谓收笔的特征是“蓄”,是讲线条的力度不要外露,要深藏其中,造就一种内在的筋力。
在观赏一幅书法的时候,我们往往会对线条的质感或厚度产生兴趣。从金文到石鼓文、秦篆,我们所看到的是满眼绝对中锋,线条厚实。特别是秦篆,笔笔圆润、笔笔厚实、笔笔圆柱形,使线条极富质感意味。到了隶书的出现,将“绝对中峰”扩散化了,行草书的问世,更是将线条的质感和厚度的诠注进行了拉伸和丰富。中锋质感总是受人关注和无可质疑的,然而“侧锋取妍”,可谓是线条质感效果的补齐和增强,奇妙的效果往往出人意料。
在宣扬了书法线条的力感、质感之后,还有一种令人心潮起伏的美——节奏感,需要大书一笔。
节奏在线条中的运行几乎与书家的心理起伏甚至生理节拍相吻合。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,但并不是我们所要反映的重点。
我们所要谈的线条的节奏感,是线条本身的内涵情愫特质与显性特征。一般来说,书家在用笔的行径中所自主展现的徐急、松紧和轻重的交叉对比,在形式上会显现出空白与墨线之比、墨线粗细、干湿、方圆、转折之比,乃至墨线的虚实与浓淡之比等等。这些对比,构成了节奏的“阴阳之比”,即节奏之本。在线条的形成之中, “藏头护尾”、“一波三折”、“起承转合”、“重顿轻变”等,都是极其珍贵的法宝,是构感节奏韵律的千古不变的技巧。通过这些技巧的运用,在书法线条意味中洋溢出书家生命律动的节奏和心理起伏的轨迹,让观者在流动式的欣赏过程中,充分感受到这一奇妙的历程与效果。这就是节奏感的妙不可言之处。
对于书法线条意味的描述仅限于此是不够的。因为力感、质感和节奏感并非泾渭分明,而是互相提携互相渗透的。实际上,我们所感受到的往往是有力度的节奏、有厚度的力感,换句话说,就是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。在书法线条组合中,没有孤立的力感、质感和节奏感,并非是排他的。
除此之外,我们在真切感受书法线条意味的时候,应更关注到书法作为艺术的灵魂所在,直白地说,就是书家的文化情愫、情感变化、精神境界的价值所在。这就是我们在对书法线条的品赏之中所最终享受的最珍贵的财富。
书法的线条美是如何表现出来的
书法的线条美是如何表现出来的,很多书家都明白,线条是书法的基础、灵魂,是书法赖以延续生命的重要媒介,也是书法家表情达意,精神、气质和学养得以流露的媒介。
汉隶的出现是书法艺术中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,没有一种书体的表现力能与它相抗衡。当然,更为直接的则是在于汉隶的主要贡献——解放线条,它对于我们研究线条美有决定性的影响。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,首先被欣赏者感觉到的也是线条,所以它也是欣赏者沟通书家的桥梁。通过线条,欣赏者可以获得精神上美的享受,心灵上的慰藉、净化和震撼。中国书法的毛笔工具为线条美的高层次塑造提供了极理想的支持。欣赏者可以把线条作为审美对象,从视觉上把握作品的深层内涵,书法家们也把线条看成其作品的一种生命象征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·碑评第十八》中,有过这样的一段论述:“书若人然,须备筋骨血肉。血浓骨老,筋藏肉莹,加之姿态奇逆,可谓美矣”。在这里,“筋”、“骨”、“血”、“肉”四者,都是针对书法线条而言。康有为认为书法线条美犹如一个人生命体的美,它体现出书法美的最高原则。在中国书法艺术领域中,书法线条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(一)力量感
这里所谈的力量感,是书法中的一种巧力,是掌、指、腕、臂在人的意识协调和控制下且融合了书写者审美观念、书写经验的自然运动。中国书法一贯强调笔力,卫夫人的《笔阵图》有云:“下笔点画。波撇屈曲,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”。东汉蔡邕则在《九势》中指出:“下笔用力,肌肤之丽”。肌肤就是线条美的形式感觉。一般而言,下笔有力,线条就美,就有丰富的肌肤内涵。“在技巧之力中仍然有明和暗的对比关系:线条头尾顿挫转折者是谓‘明’,线条中截平稳运动的貌不惊人的力是谓‘暗’”。这段话指出了线条力度美的真正所在。富有力度的书法艺术作品之所以美,是因为它能使观赏者在这种凝固而静止的字形中领略到生命的风采、心灵的律动。如果笔力弱薄,书法美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挥。
(二)立体感
对于书法这一平面的艺术形式而言,立体感是一个矛盾的说法。因为线条本身是平面化的存在,根本不可能符合三维空间的物理标准。但是一副书法作品如果缺乏立体感,线条就单薄乏味,不耐看。真正的立体感应是沉着、浑厚的并能让人感受到线条中蕴藏的丰富信息。简要地说,书法所强调的立体感是一种抽象地经过提炼的空间。在创作具体的书法作品中,又因书体不同以及书者的审美趣味各异而自具形态。强调线条要具有立体感,当然与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。任何一种审美意识都离不开社会内容的制约,书法自也不例外。如女书家卫夫人在《笔阵图》中指出:“夫三端之妙,莫先乎用笔,六艺之奥,莫重乎银钩。”这段话的推理公式是:书法——用笔为先;用笔——中锋居重;线条——要有立体感才美。
从书法美的角度来看,中锋技巧是绝对的。而侧锋技巧是相对的,它无法独立运用,只能与中锋互相交替补充。而且不能处于主要地位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书法讲求笔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线条美,而线条美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立体感要强,要有厚度。我们可以改造用笔的方法,但却无法跨过这个终极的书法美的目标。它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,而实质上是一个美的问题。
(三)节奏感
我们从书法作品的节奏感里可发现一种活力,然后在活力里面体验到了生命的价值。节奏的原则就是对比的交叉。落实在书法形式上,则是空白与墨迹之比,空白大小之比,空白形状之比,墨迹点线之比,乃至墨迹粗细、干湿、方圆、转折之比。大凡构成一种对比,都含有节奏的元素。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“阴阳”便是节奏之本。线条在构成过程中笔的运动特征——松紧、轻重、快慢,就是线条节奏的具体内容。种种运动的性质和种类也有不同,不管是何种性质的节奏,都是对比着而存在。毛笔书法能够表现出很多书法家的个性。每位书家生命的活力都体现了线条节奏感的审美价值。如:空间节奏、用笔起伏节奏、空白节奏、方向节奏等。
节奏的原则相对于力量感、立体感的原则而言,似乎显得较为简单。因为对力度和线条的厚度,我们都能从一个实际的起点出发,在外观形态上对此作深层次的描述。但对于节奏而言,可视的形态比比皆是,不可视的深层内容又不仅仅是书法方面的内容,还牵涉到生理、心理方面的问题。立体感、力量感与节奏感基本上囊括了线条审美意识的全部内容。不仅如此,即便是在书法的运笔技巧方面,“三感”的存在也已经包括了技巧的全部空间内容。
力量感的构成是依靠提、按、顿、挫、转、折、方、圆,强调的是一种用笔的起伏——上下运动;立体感的构成,则依靠中锋为主的用笔,而笔法则落实到线条美的具体范围,追求的不只是在平的纸面上画出线,而是要塑造出立体效果;节奏感的构成是依靠速度的控制、断续连贯、轻重徐疾,有个推移过程,因此具有时间属性。立体感与力量感,平面运动与上下运动,构成了立体的动作空间,再加上一个节奏感,又构成了时空对比,三者互相交叉,相互渗透,形成了书法技巧的最为广阔的艺术天地。

相关阅读

传承新章 MONCLER GRENOBLE 于阿斯彭致献未来传承
传承新章MONCLER GRENOBLE 于阿斯彭致献未来传承2026年2月1日,阿斯彭落基山脉月色浸润的群峰之下,性能与优雅交织,天然雪丘..
ROGER VIVIER 2026 春夏 PIÈCE UNIQUE 高定系列
巴黎,2026 年 1 月 27 日,星期二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,ROGER VIVIER于全新巴黎总部「RV 之家」呈现 2026 春夏Atelier Ani..
爱马仕全新发布Natures Marines海洋秘境餐瓷系列
爱马仕家居世界艺术总监Charlotte Macaux Perelman与Alexis Fabry特邀英国艺术家Katie Scott从十九世纪英国园艺图鉴及威尔士海..
24小时节律奢养,资生堂专业美发芯诗珀莉昼夜黑金系列耀目上市
汉高消费品牌业务部旗下品牌资生堂专业美发芯诗珀莉,始终秉持唤醒本真之美的品牌使命,全新推出昼夜黑金系列,以融合前沿科技..
欧米茄推出超霸系列月球表新作 黑白双色盘面重塑腕间经典
2026年,瑞士著名专业制表品牌欧米茄 (OMEGA) 以两款全新超霸系列月球表开启新的一年。每款腕表均以黑白反转表盘的布局重新演..
游戏电视怎么选?OLED VS RGB-MiniLED横评
在高端电视市场,OLED曾经一度占据画质之王的宝座。但随着技术迭代,一个更强劲的对手已经从幕后走向台前,那就是RGB-MiniLED..
反向春运不凑活!海信百吋承包三代人的快乐
团圆换种方向,反向春运又暖遍社交平台。越来越多人不再挤返乡高峰,而是把父母、孩子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既不用抢难买的返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