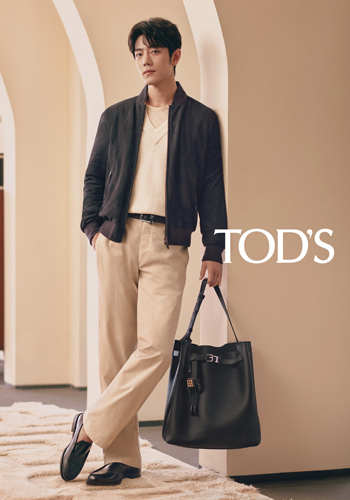不用再羡慕“钢铁侠”埃隆·马斯克了,中国第一家私人火箭公司已经在深圳诞生。
创始人胡振宇21岁,今年6月刚刚毕业。5个月前,他创立名为“翎客航天”的公司,英文名linkspace,意为连接太空与地球。
这名90后长着娃娃脸,身高不到一米七,脸上长着雀斑,志气却不小。在他的商业计划书中,甚至提到高速洲际载人交通的设想,从香港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1150千米的距离,通过搭乘载人火箭,可在40分钟内到达。
这只是胡振宇雄心的一小部分,他的目标是冲破国内封闭、垄断的航天市场——并非痴人说梦,7月他已经获得第一笔订单。从父母那儿领生活费的创始人
与公众熟悉的“长征”等运载火箭相比,翎客航天目前研发的探空火箭体形更小,通常长度不超过10米,箭体直径不超过30厘米,有效载荷数十公斤。它的作用是将搭载的仪器送到几十至几百公里的高空,进行几分钟的科学观测。飞行轨迹是“直上直下”,不需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,也不需要入轨、释放卫星等复杂动作。
探空火箭相对简单的结构和功能,让民间科研力量有望参与其中,不过,翎客航天想成为市场的主要玩家,还要加把劲。
胡振宇的公司一共包括3名员工: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、清华大学博士严丞翊,火箭爱好者吴晓飞,外加他自己。除1985年生人的严丞翊外,其余两人均为“90后”。
他们没有自己的研发基地,包括发动机在内的所有实验都需要借用清华大学实验室;虽然把公司注册在深圳,但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,而是“流动办公”,并征用吴晓飞在江苏老家的一小块地皮作为试验场。
他们更没有钱,所有经费都来自三人的积蓄,以及承接其他研究项目得到的报酬。胡振宇虽然已经毕业,但每个月仍然要从双职工的父母那里“领取”生活费,补贴在广州租房生活的成本。
窘迫的创业生活并未将他们的野心消磨殆尽。投资1600万元,换取16%的股份,这是胡振宇为翎客航天开出的价码。也就是说,他给公司的估值是1亿元。
胡振宇计划一边找钱,一边继续把从其他地方赚到的钱投入到公司。他打算在三年后推出首枚商用探空火箭,搅动长期被两大国企——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集团垄断的市场。“公司将来肯定不会卖,因为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钱,而是为了梦想。” 边“打酱油”边学技术
时光回到四年前。彼时,胡振宇刚被华南理工大学录取,身份是“网球特长生”,专业则是工商管理。他从初中开始就自学化学、研究炸药,希望有一天能够发射火箭,但这两个差之千里的“技能点”仿佛为这一梦想添加了“不靠谱”的刺眼注脚。
按照正常剧情,胡振宇将会淡忘自己的初心,顺利毕业,并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,结婚生子。然而,一个名叫“科创航天局”的民间火箭爱好者协会让他迎来转机。2011年,该协会组织了两次小型探空火箭试射,结果“万户1号”因场地和安全问题最终放弃;“万户2号”在点火时发动机爆炸,数千元的设备灰飞烟灭。
作为发起者之一,胡振宇在前两次发射中主要负责“打酱油”,同时学习技术。到了2012年1月的第三次发射,胡振宇开始做整体设计,制造发动机,并获得校友的10万元赞助。
拿到钱后,胡振宇邀请科创航天局一起制造火箭。不料,这笔小小的款项竟成为双方互相攻讦,最终分道扬镳的导火索。胡振宇和科创航天局都觉得自己才是这10万元的管理者。2013年7月,胡振宇和小伙伴们在内蒙古科尔沁准备发射代号为YT4的探空火箭,在各种扯皮下,第三次发射不了了之。
最终,胡振宇还是想办法,最终成功试射首枚“准专业级探空火箭”, 他负责了火箭的整体布局以及箭体、燃料棒和发动机设计制造。双方的矛盾再度激化,最终导致他与科创航天局决裂。
“就是一群不干事的人,看到你出名了,又没有带上他们,觉得很不爽,就想把你搞下去。”胡振宇言辞尖锐。然而根据科创航天局官网的说法,将胡振宇除名的原因包括违反安全制度、不配合评审、掩盖事故隐患和“无法沟通”等。
胡振宇为自己的精神洁癖和少年心性付出了代价。“我当时退出来,很心酸,多像乔布斯当年啊,我被自己带起来的团队开除了!”这也意味着,他不能再把自己局限在松散而混乱的爱好者社区了。他必须为自己的理想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容器,并用商业规则去培养和调教。除了红杉,国内大风投都找过我
翎客航天让胡振宇迈出从爱好到商业化的第一步。
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,国内的航天市场并非绝对禁区,也没有众多监管机构设置门槛。翎客航天的行业分类是“航天产业”,除了获取一些资质认证外,创办过程中并未受到太大阻拦。
胡振宇认为,这主要因为还没搞出名堂,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。另一方面,国内对于探空火箭并没有明确的管理条例。胡振宇的经验是,发射前向空管部门、空军等提交申请,预订航道和发射场地即可。“就像支付宝最初也打了政策擦边球一样,当我们能发展得足够强大的时候,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?”
由于“无法可依”,监管部门更倾向于事后监管。“之前的情况是,你去找他们沟通,人家都不理你。没有条文可以批准你,也没有条文去抓你。火箭掉下来砸到人,你就别想跑了;砸不到人皆大欢喜。”胡振宇说。
由于探空火箭结构简单,胡振宇和团队成员能够自行制造发动机,并组装箭体。据介绍,这种发动机的结构甚至比汽车发动机还要简单,而箭体材料在公开市场上就能买到。
唯一的麻烦是火箭燃料。这种燃料与导弹和航天飞机使用的固体推进剂完全相同,属于危险品,个人需要通过特殊途径购买,还要在公安局备案。翎客科技则是由严丞翊出面,以清华大学的名义购买,程序就简单了很多。
公司成立后,胡振宇除了继续搞研发,还增加了一项重要工作:寻找风投。计划中的1600万元天使投资,能够支撑翎客航天未来3年的研发和人员开支。目前,已经有多家风投表达了兴趣。胡振宇对此颇为自豪:“国内大的风投都来找过我们,除了红杉资本,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。”
然而,投资意向并不等同于真金白银。大多数投资人并不了解探空火箭,胡振宇常常需要向投资人普及航天知识,给他们阐明探空火箭与运载火箭的区别。他最常听到的问题是:“你能卖给我一张(宇宙飞船的)船票吗?我想预订一张。” 做中国版SpaceX
虽然距离真正的商业化还很远,但胡振宇已经为翎客设定了核心竞争力——性价比。他希望效仿眼下大红大紫的美国同行SpaceX,冲击被国企垄断的航天市场。
目前,国内只有一家公司提供探空火箭服务——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第四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航天四院”),每次发射报价300万元。
作为一家“体制内”的研究所,航天四院有多级承包商,中间有很多抽利过程。翎客航天则希望尽可能自力更生:“能自己做的,全都自己做,从源头上解决供应的问题。采购的东西只占20%,火箭燃料、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完全自主。”
不过,对航天四院而言,压缩探空火箭成本,远不如发射卫星赚钱,因此也没有太大的投入意愿,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往往滞后。这被胡振宇视为发展契机,翎客航天计划把价格拉低至200万元,同时提供更好的性能。其中的关键则是缩短供应商链条,减少分包成本,避免层层倒手、加价,以确保毛利润率。
负责系统技术的严丞翊举例称:“一枚探空火箭价值300万元,但上面的载荷可能价值上千万,现在基本上用一次就废了。我们就可以做到载荷回收,甚至让火箭原路返回。”
目前,探空火箭的主要客户是高校和科研院所,而传统国企在争夺这类客户时优势明显。不过翎客航天并不担心被垄断扼杀:“军用产品必须有军方背景,民用产品则更倾向于开放市场。国企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关系网,能够渗透到所有高校。此外,探空火箭可以出口,比如提供给东南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。”
私人火箭在中国是一片庞大而未被开发的处女地。根据美国Space Foundation研究机构的报告,2012年全球航天领域相关的市场规模达到3040亿美元。在美国,已经有商业运载平台SpaceX和提供亚轨道旅行产品的维珍航天。但在中国,翎客航天之前尚无私营航天公司出现。
这名少年能冲击被垄断的航天市场吗?去年火箭发射前,胡振宇一直被梦魇困扰,梦里他孤身一人走向荒漠,“3、2、1,点火……”一声巨响,火箭没有腾空而起,只剩遍地碎片。他从梦中哭醒。如今,他自信了很多,“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真正把它当做事业来做”。

相关阅读

舞者杨文韬&Cici:感受与自然的连接,舞动“韧性”故事
编舞师、舞者 杨文韬Taotao张灿Cici 在山兰稻田中创作舞蹈Greenpeace/Yan Tu语言的表达是直接的,但舞蹈不一样。我们通过编舞..
传承新章 MONCLER GRENOBLE 于阿斯彭致献未来传承
传承新章MONCLER GRENOBLE 于阿斯彭致献未来传承2026年2月1日,阿斯彭落基山脉月色浸润的群峰之下,性能与优雅交织,天然雪丘..
ROGER VIVIER 2026 春夏 PIÈCE UNIQUE 高定系列
巴黎,2026 年 1 月 27 日,星期二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,ROGER VIVIER于全新巴黎总部「RV 之家」呈现 2026 春夏Atelier Ani..
爱马仕全新发布Natures Marines海洋秘境餐瓷系列
爱马仕家居世界艺术总监Charlotte Macaux Perelman与Alexis Fabry特邀英国艺术家Katie Scott从十九世纪英国园艺图鉴及威尔士海..
24小时节律奢养,资生堂专业美发芯诗珀莉昼夜黑金系列耀目上市
汉高消费品牌业务部旗下品牌资生堂专业美发芯诗珀莉,始终秉持唤醒本真之美的品牌使命,全新推出昼夜黑金系列,以融合前沿科技..
舞者杨文韬&Cici:感受与自然的连接,舞动“韧性”故事
编舞师、舞者 杨文韬Taotao张灿Cici 在山兰稻田中创作舞蹈Greenpeace/Yan Tu语言的表达是直接的,但舞蹈不一样。我们通过编舞..
海南文旅消费春节档火热收官,中免集团以“免税+”激活自贸港消费新动能
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春节假期,海南文旅市场迎来消费高峰,旅游与购物热度空前攀升。丰富的新春文化体验叠加政策红利,..